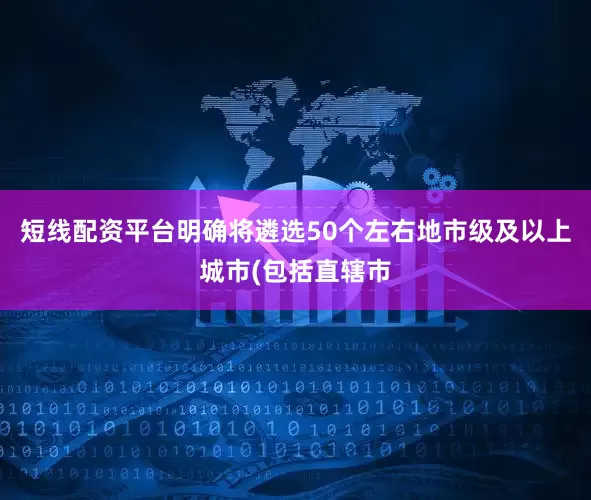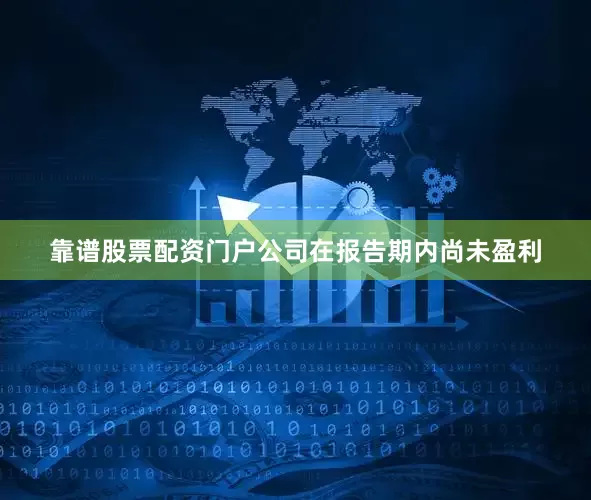01
1998年,香港回归祖国刚满一年,表面上依旧是亚洲金融中心的耀眼明珠。
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灯火通明,摩天大楼鳞次栉比,街头巷尾的人们忙碌穿梭,楼市和股市的繁荣让许多人相信,这座城市将继续腾飞。

然而,在这片繁华背后,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。
远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,已如野火般蔓延,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国接连沦陷,经济体系被摧毁殆尽。
而主导这场浩劫的,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国际炒家,他们在东南亚赚得盆满钵满后,将目光投向了香港——“亚洲四小龙”中最后一块未被触及的肥肉。
这场危机的源头,可以追溯到1997年7月2日。
那一天,千里之外的泰国政府在苦苦支撑后,终于放弃了固定汇率制,改为浮动汇率制。泰铢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,大量货币涌入市场,价值迅速贬值。
紧接着,物价飞涨,通货膨胀席卷全国,货币变得一文不值。
企业成批倒闭,工人失业,金融系统脆弱不堪,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陷入混乱。
街头的人们从手头拮据到食不果腹,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。
这一切,仿佛一块肥沃的土地被洪水冲垮,庄稼连根拔起,土壤养分流失殆尽,只剩下一片荒芜。
而制造这场灾难的幕后黑手,正是以乔治·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。
索罗斯,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,后移民英国和美国,1970年与罗杰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,积累了巨额财富。
他被泰国总理怒斥为“吸取人民鲜血的经济战犯”,这一称号并非空穴来风。
早在1992年,他通过做空英镑,导致英镑大幅贬值,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,索罗斯从中获利超过10亿美元。
1994年,他又将目标转向墨西哥,致使墨西哥外汇储备告急,放弃固定汇率,货币和股市双双崩溃,量子基金再次满载而归。
索罗斯的策略并不复杂,却极具破坏力。
以泰国为例,1996年底,泰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后,金融体系问题频出,高额外债、长期逆差和猛烈通胀成为致命弱点。
这些漏洞,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。他先从泰国银行等机构借入大量泰铢,然后抛售到外汇市场,换取美元。
大量泰铢涌入市场后,价值不断下跌,索罗斯再以少量美元低价回收泰铢,还清借款。这一借一还之间的差价,直接进了他的口袋。
泰铢跌得越狠,他赚得越多。
尽管泰国政府动用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回收泰铢,甚至严禁银行借出货币,但仍无法抗衡炒家的攻势。
最终,泰国仅剩28亿美元储备,彻底失去抵抗能力,泰铢在一天内暴跌20%,此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索罗斯和他的团队,在这场洪流中获利数十亿美元。

然而,高额利润并未满足他们的胃口,反而让他们更加贪婪。短短几个月内,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继被金融风暴吞噬。
曾经名噪一时的“亚洲四小虎”,无一例外损失惨重。风暴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,继续席卷韩国、日本、中国的台湾地区,最终指向香港。
这就是20世纪末横扫亚洲的金融大危机。
香港,作为亚洲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和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,拥有近万亿美元的境外资产,占全球的8%。
1997年上半年,香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,楼市和股市不断创下新高。
新楼盘开售时,前一晚就排起长队,港股恒生指数在7月最后一天突破16000点,创下历史纪录。
然而,这座城市并非无懈可击。
巨大的楼市泡沫、偏高的家庭负债、企业过度依赖借贷、严重的贸易赤字,这些问题早已埋下隐患。
而国际炒家们,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
索罗斯和他的同伙,并未急于动手。他们深知香港根基深厚,拥有近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远非泰国可比。
因此,他们选择耐心布局,暗中囤积港元和期货合约,等待最佳时机。
他们的野心,不仅仅是小打小闹,而是布下更大的局,企图一口气吞下香港。
如果香港真的成为下一个泰国,后果不堪设想。
富人资产大幅缩水,股票成为不定时炸弹,公司和工厂被迫关闭,资金外流加剧混乱;中产阶级惶恐不安,卖房却无人接盘,旅游和私立学校等开支被取消;底层民众更是雪上加霜,从一日三餐到食不果腹,从低薪工作到彻底失业,生存希望被彻底掐断。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,国际炒家犹如伺机而动的猎手,而香港这座城市,尚在繁华的梦境中未曾醒来。
危机已如乌云般笼罩天际,风暴的前奏悄然奏响。
02
1997年7月中旬,香港的街头依旧车水马龙,市民们沉浸在回归祖国后的喜悦与经济繁荣的氛围中。
然而,国际炒家们已经悄然行动,开始对港元进行试探性冲击。
首批少量国际资本流入市场,试图测试香港的防御能力。
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应,仅动用了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配合一些常规政策,就将局势稳定下来。这次小规模交锋几乎未引起波澜,普通市民甚至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,继续在楼市和股市的热潮中追逐财富。
国际炒家们并未因初次试探的失败而退缩。他们清楚香港的底蕴,也洞悉其弱点。暗中,他们继续囤积港元和期货合约,等待更合适的时机。
果然,到了8月中旬,他们发起了第一轮正式冲击。
8月15日和16日两天,炒家集中抛售了40亿港元。港元与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,自1983年以来,美元兑港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7.75到7.85之间,以确保货币稳定。
这次冲击下,15日当天汇率一度逼近警戒线,恒生指数下跌2.43%。
接下来的交易日,恒指跌破16000点大关,并在9月初进一步下滑至13000多点。

面对这一波攻势,香港金融管理局并未慌乱。凭借近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金管局动用美元回收市场上过多的港元,同时提高利率,再次化解了危机。
表面上,局势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
然而,东南亚其他市场的喘息并未持续太久。
10月17日,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短暂的宁静:台湾当局弃守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,几天内新台币跌至10年新低。
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,国际炒家以索罗斯为首,抓住时机,准备对香港重拳出击。
10月21日起,国际资本连续三天抛售了共计1000亿港元,规模之大前所未有。
美元兑港元的汇率再次逼近警戒线,市场恐慌情绪迅速蔓延。
香港市民开始感受到危机的真实威胁。泰国人民的惨状历历在目,若港元沦为泰铢的下场,他们的生活将彻底崩塌。银行门口挤满了人,市民争先恐后将手里的港元兑换成美元。
对他们而言,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,兑换外币成了自保的最后手段。
为了稳定市场和民心,香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。
时任香港金管局总裁的任志刚,决定在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元同时,紧急调高港元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。
这一策略被戏称为“任一招”,旨在增加国际资本借贷港元的成本,抑制做空风险。通常情况下,这一利率不到5%,但在那一天,数字飙升至300%。
几天后,一个月期的拆借利率回落至10%以上,但仍远高于正常水平。
尽管汇率得以保住,股市却未能幸免。
10月23日,恒生指数大跌1200多点;到了28日,再次下跌1400多点,最终跌至9000点大关。
股民们尽管此前听闻过经济危机的传言,也收到过不少警告,但真正身处其中时,才感受到切肤之痛。
那时的股票交易不像如今可以通过手机操作,信息获取渠道也极为有限。等到许多人反应过来,准备卖出股票时,早已为时已晚。
大量股民一夜之间破产,积蓄化为乌有。
期货市场同样失守,10月中旬,恒指期货未平仓合约达到6万张。
短短7个交易日内,国际炒家通过股指期货交易,浮利超过130亿港元。而香港十大富豪的损失,则高达2100亿港元以上。
楼市也未能逃过冲击,整个香港经济弥漫着压抑的气氛。
明星钟镇涛早年热衷炒楼,曾赚得不少,眼见前景大好,他借入高额贷款准备大展拳脚。
然而,这场风暴让他的投资血本无归,还背负了2亿多港元的巨债。

普通市民的处境更为艰难。
某知名地产公司的两名秘书,在危机前各自购置了一套公司房产,首付三分之一,共花费80万港元,这是她们工作10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
几个月后,房子尚未入住,价值已贬至80万港元,仅剩原价的三分之一。她们不得不放弃房产,否则还需向银行偿还160万港元的贷款。
类似的故事,在当时的香港比比皆是。
这场金融风暴,将香港变成了国际炒家的提款机。
市民蒸发的资产,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战利品。
政府虽然暂时守住了港元汇率,但经济各领域已伤痕累累,市民的信心开始动摇。
国际炒家的攻势并未停歇,他们的下一步计划,正在暗中酝酿。
03
1998年初,亚洲金融危机的烈焰继续燃烧,国际炒家以索罗斯为首,在东南亚各国留下一片焦土。泰铢贬值56%,印尼盾贬值85%,韩元兑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,马来西亚被迫实施外汇管制,日元承压加剧。
泰国、印尼和韩国甚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。
韩国动用了几乎全部外汇储备,仍无济于事,政府濒临破产,1998年初还发起了“全民捐金运动”。
而香港,尽管在1997年10月的冲击后暂时稳住阵脚,却未能真正摆脱威胁。
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开表示,政府将坚决维护港元的联系汇率,高涨的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只是暂时的,调整也是短期的。
在其后约两个月内,恒生指数在10000点左右徘徊,香港金融市场看似恢复了稳定。
然而,国际炒家的围猎从未停止。
1998年初,印尼金融市场再起波澜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方案未能阻止其经济陷入史上最严重衰退。
受此影响,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韩国等国的货币再次暴跌。
在这背景下,索罗斯等炒家对港元发起了新一轮狙击。年初和6月,他们持续加码攻击,尽管在高利率的支撑下港元汇率得以保住,但银行、楼市、股市和期货市场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香港最大的投资银行“百富勤”在1月宣告破产清盘;

到了7月,香港房价整体下跌近50%,一些价值上千亿港元的别墅跌至300多万港元;
股市每日平均交易额从去年的150亿港元跌至40亿港元,恒指跌入7000多点;
恒指期货未平仓合约逐渐增至近10万张。
民生方面更是雪上加霜。香港失业率攀升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,家庭汽车被拖走,还不起贷款的房屋被银行收回,许多人被迫从城市搬到农村。
媒体报道中,“自杀”和“跳楼”的字眼频频出现。
据统计,这场危机期间,香港的自杀率上升了40%。
昨日的繁华,仿佛成了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境。
经济若继续恶化,香港可能面临致命打击,但若放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,后果同样不堪设想。
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原本与妻子在伊斯坦布尔度假,却频频与香港方面通电话。
行程未尽,他便以要事为由赶回香港,留下妻子独自在异国。
政府内部已隐隐预感到,这只是开始,更艰难的挑战还在前方。
8月初,量子基金和其他国际资本再次准备了大量港元,在外汇市场发起冲击。
这一次,金管局不再过度依赖利率调整,而是更多动用外汇储备应对。
8月5日和6日两天,国际资本各抛售了200多亿港元,政府全数吸纳这些流入市场的港元并存放回银行。
尽管利率未有大幅波动,股市却难以幸免。
8月7日,恒生指数狂泻至7018点。去年同一天,恒指尚处于16673点的历史最高峰,一年之间,香港总市值蒸发了2万亿港元。
当天,董建华发表公开讲话:“如果有人觉得我们会有所动摇,他们是错的!我们绝对有能力与决心维持联系汇率,我们一定会做得到。维持联系汇率将能确保香港的长远经济活力与利益,短期的痛苦可以接受。”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国际资本连续出击,至8月13日,恒指跌至6660点。
尽管政府死守港元汇率,炒家表面上未获大利,但他们的真正目标逐渐浮出水面。
香港政府发现,这波操作看似攻击港元,实则剑指股市和期货。在发起冲击前,炒家先造势推高股市,借入大量股票和期货,建立巨额空盘。
待政府为应对港元贬值采取措施后,他们趁机抛售股票,引发股指和期指大跌,从中渔利。这种策略与做空货币有相似之处,但操作更为复杂隐秘。
他们还提前囤积港元,即便面对政府对策,也能将损失降至最低。
这种双线操控的手段,比在泰国时的单一做空更为精明,既能绕过香港的利率防御,又能利用汇市和股市相互施压。
他们深知香港的优势与弱点:外汇储备丰厚,港元难以撼动,但作为自由港,香港奉行自由市场原则,政府无法直接干预股市和期市,只能任由他们操控。
显然,为了这盘大棋,国际炒家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香港政府面临的,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,更是一场策略与意志的较量。
04
1998年8月,香港的金融市场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国际炒家接连冲击,恒生指数跌至历史低点,市民信心几近崩溃。
早在1997年10月的交锋中,香港财政司就察觉到炒家的真正目标并非港元,而是股市和期市,只是当时缺乏足够证据。
年初的几轮攻击进一步暴露了危机,但形势尚未迫在眉睫,政府未采取极端措施。
然而,8月初的连续冲击让局势再也无法拖延。政府意识到,炒家的活动正在摧毁香港投资者的信心,甚至动摇自由经济体系的根基,必须采取非常手段。
8月14日,星期五清晨,香港中环中银大厦13楼“中国会”餐厅的一个包间内,气氛异常紧张。
香港三大证券商的主事人临时接到紧急邀请,聚在此地。他们脚下是香港最昂贵的土地,周围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,但此刻无人有心关注这些,只等着邀请者现身。
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陈德霖只身走进包间,请他们喝完咖啡后,要求关掉手机,并将他们带至金管局办公室。
在所有人承诺严格保密后,陈德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策: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直接干预市场,在股市和期货市场上展开反击。
这并非临时起意,而是经过周密讨论和计划后的艰难抉择。
面对防线即将崩溃,政府的选择不多:继续动用外汇储备和提高利率防守港元,可能重蹈泰国覆辙,导致金融体系崩塌;
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治标不治本,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灾难;
放弃联系汇率制度等于向炒家投降,后果不堪设想;
唯有直接干预市场,既能保住港元汇率,又有望稳住股市和期市。
然而,这一选择充满风险。
香港经济的繁荣依赖自由市场原则,破坏这一原则可能让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失去竞争力;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明确禁止外汇管制,干预股市将加剧国际舆论的批评和信任危机;
更重要的是,政府入市缺乏经验,操作流程、法律风险、干预底线及突发情况的应对方案皆是未知,若失败,后果难以承受。
尽管如此,政府别无退路。
经过数日商讨与计划,8月13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、财政司司长曾荫权、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人签署了入市计划。
曾荫权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:“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。我既作了决定,便要坚守原则,接受批评。我会加倍努力,好向香港人交代。……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。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。”
战斗随即打响。
8月14日,三名证券大佬接到陈德霖指示,立即返回公司为金管局开设股票和期货交易账户,配合入市行动。开市前半小时,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曾荫权通知,获悉政府干预决定。
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迅速成立,独立管理政府股票交易。
金管局设立临时交易室,由可靠人员组成“战事”小组,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。买入对象主要是恒指成分股和恒指期货,紧盯现货和期货市场变动,随时调整策略,以最低成本稳住股市。
多家上市公司也联手回购股份,配合行动。
上午,股市仍呈低迷态势,但午后奇迹出现,恒指逆势反弹。
国际炒家始料未及,当天收市前,大部分人尚未察觉背后原因。
为确保保密性,陈德霖派不知情同事打探市场反馈,未发现政府入市的消息。
当天,港股上涨564点,涨幅8.5%。
收市后,为解释行动并尽量维持自由市场规则透明度,董建华和曾荫权发表公开声明。
董建华表示:“为了令经济有一个健康而有效的调整,稳定的利息十分重要。财政司司长今天指示了金管局动用外汇基金,在股票和期货市场采取适当行动,令投机者成本增加,希望他们知难而退。”
国际金融界对此震惊,美国等相关部门公开指责干预行为。
当晚,中央新闻联播发表讲话:“中央全力支持香港,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动摇。”
早在3月,中央政府已郑重宣布: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,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,坚持人民币不贬值。”
这不仅是一句承诺,更为香港注入信心。
8月15日至16日周末休市,17日因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港股再休一天,躲过全球股市暴跌一劫。
接下来三天,全球股市反弹,香港政府步步为营,击退炒家攻势。
国际炒家建仓成本在恒指期货7500点左右,8月20日恒指涨至7742点,防线进一步巩固。
21日,炒家反击,收盘前几分钟外资证券商发难,恒指一分钟内狂跌200点。
24日,政府重新集结力量,恒指和期货剧烈波动,一度短时暴跌300点,最终在金管局与证券商操作下,恒指拉升至7845点,期货逼近8000点。
炒家转而利用媒体攻击政府,试图借助国际舆论阻止干预,但政府决心未动摇。
更多证券商加入行动,中资机构也接到通知全力支持护盘。
8月26日,政府与炒家按原节奏买卖,下午15点政府突然收起买盘并抛售期货,部分炒家跟风抛售,两分钟内恒指急跌160点,期货跌近300点,随后政府大量买入,收盘时恒指仅跌55点。
27日,美国、拉美、欧洲股市下跌,索罗斯助手对媒体宣称“香港必败”。
上午开盘,国际资本涌出,半小时交易额逼近30亿港元。政府委托10家机构,在33家恒指成分股和期货上围堵,投入200亿港元,当天恒指拉升88点。
8月28日,决战之日,天文台发布雷暴预警。
上午10点开市,炒家抛售重磅成分股“香港电讯”和“汇丰控股”,五分钟交易额突破30亿港元。政府照单全收,恒指在7800点上下浮动,半小时交易额超100亿港元。
上午收市前,炒家再抛“长江实业”“中国电讯”等蓝筹股,欧洲基金加入,半天成交额超400亿港元。
下午,炒家加大火力,恒指瞬间跌300点,政府迅速拉回7900点。
最后关头,炒家集中攻击“汇丰控股”,政府再投300亿港元死守。
16点收市,恒指定格7829点,交易额790亿港元创纪录,期货7851点。
炒家损失惨重,索罗斯量子基金亏损约8亿美元。
9月后,部分炒家将期指合约转仓至9月,政府继续推高期货价格。
9月5日,金管局颁布7项措施限制投机,9月7日制定30项新规加强市场秩序,恒指大涨近600点,重回8000点。
炒家在持续亏损中退出,量子基金盈利出现罕见负增长。
香港同业拆息利率降至4%,后至1%,金融市场复苏。
政府投入股市的1200亿港元在一年内退出,盈利数十亿美元。
1999年12月6日,恒指重回16000点,香港经济进入新阶段。
参考资料:
《亚洲金融风暴:香港金融稳定保卫战》,香港金融管理局,陈德霖
《回顾香港在面对逆境中的一年》,曾荫权
《捍卫香港的货币稳定》《应付金融危机》,任志刚
CCTV「直通香港」特别节目:《香港金融保卫战》
优秀炒股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